我們買書,除了要讀好之外,還要更加愛惜書籍,對它們也要進行保護。
就算是Google的負面新聞,我也是把她當好消息來看。畢竟她還是有那麼多媒體那麼多人去關注她。在爭議中前進,歷經打磨,才能使之成熟並趨之完美。
作為一介小民的我,卻對於那些敢於吃第一口螃蟹的人總是心存敬畏之情。有了網絡後,一切都可以分享,當然也包括了書籍,誰不想吃“免費的午餐”?“數字化圖書(館)”,就像90年代末接觸網絡開始聽說有“搜索引擎”這個概念那樣咋呼起來就令人興奮,何況Google已經在努力將這一工程變成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盡管這一計劃在實施中產生了這樣那樣的問題,但相信會有一天得到解決的。
對於稍微關注互聯網和IT業界消息的同學來說,相信近日對有關Google數字圖書(館)的新聞應該略知一二了吧?!如果還不知道,可以參照以下幾則鏈接消息:
1)Google “圖書館工程”為什麼阻力這麼大?
2)“Google圖書館”遭默克爾反對
3)穀歌圖書館版權之爭蔓延到中國
4)網絡三巨頭共抗穀歌數字圖書館
還是那句話,一切都是利益使然,才導致書籍作者.出版商和Google三方之間的博弈。為了知識的共享這一崇高和理想的人文目標,如何讓Google處理好版權利益或化解壟斷之嫌疑,的確給決策層一定的壓力。在眾口難調,眾說紛紜之際,謝爾蓋.布林(Google的創始人之一)站了出來並選擇在《紐約時報》上發出了自己見解,讓我們大致了解到這個偉大的公司從圖書館藏書的歷史和現狀中看到的創想和遠景,從而對數字化圖書計劃的初衷也加深了印象。
——————以下為轉載——————
標題:一座永遠的圖書館
發表者:謝爾蓋•布林(Sergey Brin)
轉載自《紐約時報》
鏈接:穀歌黑板報
2009年10月8日,山景城,加利福尼亞
“電車沒有得到普及的根本原因在於(1)生產商的失誤:他們沒能恰當地向大眾宣傳電車的實用性;(2)電力公司的失誤:他們沒能提供足夠多的充電站和變壓站,讓人們更為方便地擁有和使用電車。早期電車在速度、行駛裏程和實用性上的限制給人們的印象至今依然存在。”
這個引述一點也不會讓那些了解電車的人感到吃驚。不過,如果這些話是在一個世紀之前聽到的,那時電車年產量僅有幾千或上萬輛的時候,可能就會有些驚人了。這是出現在1916年的一本雜志《電氣世界》(Electrical World)某期上的一個議題,是我在可供人們搜索上千萬本圖書的資料館——“穀歌圖書(Google Books)”上找到的。關於當代的一個問題要回顧幾百年來探討,看似很奇怪,但是我常常覺得過去對於未來有著極為寶貴的借鑒意義。在這裏,我很幸運—— 20世紀早期,關於電車的研究和記載非常廣泛,而且有很多關於這一主題的書可供選擇。因為1923年之前出版的書都是公開的,我很容易查看到它們。
但是人類已經撰寫的絕大多數圖書並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得到的,除非是那些在一流學術圖書館(premier academic libraries)中執著工作的研究人員。1923年之後所著的書籍很快消失在圖書館“黑洞”。除了個別特例,讀者只能在圖書出版銷售的幾年之內買到這些書,之後,只能在少數圖書館、二手書店找到它們。再往後,隨著歲月流逝,合約被丟棄了、遺忘了,作家、出版商消失了、不見了,版權所有者的蹤跡也難以尋覓。
不可避免地,僅存的幾本書也只能慢慢腐化,或者在大火、洪水或其他災害中失蹤。1998年我在斯坦福大學的時候,洪水損害、毀壞了上萬本圖書。不幸的是,這樣的事時常發生——一場類似的洪水20年前就曾在斯坦福發生過。你可以在1980年出版的《斯坦福-洛克希德•邁耶圖書館洪水報告》(The Stanford-Lockheed Meyer Library Flood Report)中讀到這段經曆,但是這本書再也找不到了。
圖書是世界共有知識、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穀歌聯合創始人拉裏•佩奇(Larry Page)在10年前就首先提出了將所有書籍數字化的建議,那時的穀歌還是一家羽翼尚未豐滿的新公司。那時,這項工程看起來如此狂妄自大、充滿挑戰,我們無法吸引人們加入進來。但是五年以後,也就是2004年,“穀歌圖書”(Google Books)(當時被稱作Google Print)誕生了,可以讓用戶搜索到幾十萬本圖書。今天,這個數字已經超過了一千萬,並且仍在增加。
次年,我們受到了美國作家協會(Authors Guild)和美國出版商協會(Association of American Publishers)對於這個項目的起訴。雖然我們之間有分歧,但卻也擁有共同的目標,那就是打開禁錮在無數絕版書籍中的智慧,當然也會公平地對版權所有人進行補償。於是,我們共同努力達成了和解,以實現我們的共同目標。這一協議旨在讓圖書作者、出版商和穀歌實現共贏,不過實際上真正的贏家是那些能夠獲得一片極為寬廣的書籍天空的廣大讀者們。
這一協議也是頗受爭議的,很多團體都積極發表意見,褒貶皆有。我想借此機會來澄清關於協議的一些事宜,並且說明我對這個計劃感到自豪的原因。這項協議旨在讓成百上千萬絕版但受版權保護的書籍“複生” ,或者會對讀者收取一定費用,或者在廣告支持下免費,但是大多數收入會歸版權持有人,無論是作者還是出版商。
有些人說這個協議類似一種強制許可證,就像集體訴訟和解一樣,如果會員在某一規定日期之前不提出退出,那麼該協議將對所有會員有效。而事實是,版權所有人可以在任何時候設定圖書價格及訪問權或者從“穀歌圖書”退出。對於那些版權所有人尚未出現的圖書,將會為其制定合理的默認價格和訪問規則。這既讓讀者能夠讀到尚未找到版權持有人的“ 孤品”,也能為版權所有者不斷累積資金,直至成為他們“不再隱身”的動力。
其他人對於協議在競爭方面的影響產生了質疑,或者斷言這會限制消費者對絕版圖書的選擇。事實上,這項協議根本沒有限制其他公司或者組織作出類似的努力。此協議在絕版圖書方面對消費者選擇的限制,也只不過像是限制消費者選擇傳說中的獨角獸那樣。如今,如果你想要得到一本絕版圖書,只有一個選擇——飛到美國幾所一流的圖書館,並期待著能在書架上找到它。
我希望能有一百種類似服務,那樣我就能很容易地閱讀到某一本書;那樣將會節省很多時間,而且會為穀歌省掉很大力氣。但是,盡管如今有不少數字化項目正在進行(穀歌甚至為其他一些同類機構提供資金支持,包括國會圖書館的一些機構),但是沒有一個頗具規模,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就是因為沒有其他人選擇為必要資源進行投資。如果想要有一百個這樣的項目,那現在至少要有這樣一個服務存在。
如果“穀歌圖書”成功了,其他項目也會效仿,那麼他們將會有捷徑可走:這個協議創立了“圖書版權登記簿”(books rights registry),鼓勵版權持有人現身,這樣其他項目將可更方便地獲得許可。雖然新項目不會立即對無人認領的作品(或“孤品”)享有同等權利,但至少這個協議為類似訴訟的和解提供了方向,而且它是“孤品”的立法先驅,穀歌一直並將繼續為此提供支持。
最後,對於“穀歌圖書”這一產品以及協議中所展望的未來服務的具體幾個方面還有反對的聲音,包括對於文獻目錄信息質量、我們對於分類系統的選擇以及隱私條款細節的質疑。這些都是合理的問題,作為一家極為關注產品質量的公司,我們會不懈努力來解決這些問題,不斷完善文獻目錄信息、改善分類方法,進一步細化我們的隱私條款。而且,如果我們不能正確提供產品,就會被其他人取代。但有一件事可以確定:無論停止哪項進程,事情最終都不會得以解決。
我在“穀歌圖書”上找到的《1880-1881保險年鑒》(Insurance Year Book 1880-1881)中,Cornelius Walford按照時間順序記載了幾十座圖書館和幾百萬冊圖書的毀滅,他希望這樣的記載能夠讓人們意識到做這樣一些事來保存圖書的必要性。亞曆山大一個著名的圖書館曾發生過三次火災,分別在公元前48年、公元273年和公元640年,就像美國國會圖書館一樣,1851年的一次大火燒毀了三分之二的藏書。
我希望這樣的毀壞永遠不要再發生了,但曆史證明並非如此。更重要的是,即使我們的文化遺產在世界最一流的圖書館保存得完好無損,但是如果不能讓人們輕易讀到,那也形同虛設。很多公司、圖書館和組織在保存、提供20世紀藏書的工作中都發揮了作用。圖書作者、出版商以及穀歌,他們共同朝著這個目標邁出了僅僅一步,但卻是非常重要的一步。讓我們抓住這次機遇,不要錯過!
謝爾蓋•布林(Sergey Brin)是穀歌的聯合創始人和技術總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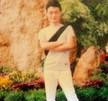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